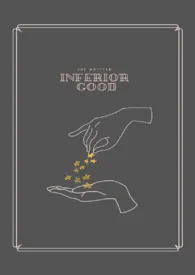天色将暮,义军新营尚未完全安顿,外头荒村狼迹遍地,难民如潮。
前几日粮车连续失窃,哨兵都紧绷着神经,夜夜守营,防贼亦防匪。
那夜风高,营中一片昏黄,婉婉亲自点检新进药材与布匹,回帐时已过戌时。裴琳一整日跟着她巡视,嘴上虽不甘,却也强撑着不肯示弱。
「好累……」裴琳坐在帐外的小台阶上抱怨,见身后那辆运送干粮与药品的大马车无人看守,竟倚着马车边攀了上去,说声「我就歇一下」,竟蜷着身子睡了过去。
婉婉本想唤她,却见她熟睡模样竟有几分孩气,思及裴玄近日也常说她娇纵难驯,婉婉只轻轻盖了件披风,未惊动她,便转身离去。
**
深夜三更,突有急促马蹄与喊杀声破风而来。
「不好了——物资马车被劫走了!」
有兵卒狂奔来报,声嘶力竭。
婉婉闻言脸色骤变,当即回头:「裴琳在那辆车上!」
话音未落,她已跃上马背,抓过一张长弓与箭囊,脚一磕马腹,毫不犹豫地奔出营门。
夜色深沉,荒道两旁是低矮灌木与碎石坡。前方隐约见得车辙与尘烟,远处几道黑影扯动缰绳,正欲将马车推往山间密林。
婉婉弓身伏在马背,心中一念疯长:「不能再错过一次……这次,我要亲手把人带回来!」
她急策而上,口中高喊:「住手!放了她!」
喊声惊动山匪,几人抽弓便射,一箭擦过她耳侧,险些划破面颊。她不惧,反倒纵马更近。
马车上传来一声惊叫,是裴琳。
她身影跌跌撞撞地从干草堆里探出身来,泪眼模糊,满脸惊惧:「婉婉——救我!」
婉婉翻身下马,拔剑朝车侧冲去,单手高举火把欲吓退山匪。混乱中,她见裴琳正勉力伸出手,赶忙跃起去拉她。
两人指尖相触之际,婉婉猛然感觉上方一凉。
一根箭矢带着死亡的气息,破空而来,直直朝她胸口袭来!
一瞬之间,她几乎来不及转身,只能用身体挡住裴琳。她想:若今日死在这里,也算还了某些亏欠。
可下一刻,一道黑影如闪电般飞掠而至,沉喝声自风中爆开:
「婉婉——小心!」
长剑出鞘,剑光闪处,虽断箭未果,却稍偏其势,箭仍不偏不倚,深深刺入那黑影的左肩。
「——裴玄!」
婉婉惊呼。
裴玄咬牙不语,一手揽过她与裴琳,将两人护在身后,右手仍稳稳执剑,面对山匪毫无退意。
山匪见主帅在场,且义军后方已闻风而至,心知不敌,忙惊惶四散而逃。
四周终于平静。
裴琳瘫坐在地,脸色如纸,眼里尽是震惊与羞愧。
婉婉则手忙脚乱地按住裴玄肩上的箭伤,想撕布为他止血,却又怕动作不慎加剧伤势,急得眼眶发红。
「我……我来迟了。」裴玄低声说,语气却轻如呢喃。
他望着她,唇角微弯,像是在安慰,又像是在自责。
「你来得刚刚好……再晚一刻,我便……」她嗓音颤抖,却说不下去。
裴琳在一旁看着这一幕,怔怔出神。
她原本以为婉婉的温柔只是手段,是为了讨好表哥;她原以为表哥的信任只是暂时,是出于职责。可此刻她明白了:
那不是客套,也不是怜悯。
是裴玄甘愿负伤,也要护她周全。
而那女子,竟在千钧一发之时,毫不犹豫地为她冲上来。
她低下头,弱弱地问:「妳......我待妳如此无礼,妳为何救我?」
婉儿温柔着说:「妳若出事,裴将会难过的……而且……我知妳心地其实纯善,那天兵士带回一个满身脏污的难民,全身臭得难闻,腐烂的伤口散发着血腥的腐臭味,连营内见多识广的大姨们都不住干呕……偏偏妳走过去,竟什么都没说,只蹲下来替那人解开脚上的破布,还自己去端了一盆水来,一点也没嫌恶地清洗。」
婉婉顿了顿,声音轻柔却坚定:「那时我就知道,妳不是坏人。只是太在意妳的玄哥哥了,怕被人夺走妳在他心里的位置,才会说出那些难听话。」
裴琳听完已经泣不成声:「对不起……真的很对不起。」
众人返回了军中,裴琳坐在房外的木桩上,双手紧紧握在膝头,十指紧扣,指节泛白。
她从未像此刻般羞愧难安。
方才惊险宛如梦魇,她甚至不敢回想自己是如何瘫在马车上、哭着伸手,任由那个她曾百般揶揄的女子为她冲入箭雨中。更不敢想,若裴玄再慢一步,她与婉婉会否双双命丧山道。
裴琳自小骄纵,万人捧在手心,性子不坏,却心高气傲。她从未向谁低过头,更不曾说过「对不起」。
可此刻,她知道,她欠了婉婉一条命。
门帘忽动,婉婉捧着一碗热汤走来,手里还拎着两块烤饼,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般,坐到她身边。
裴琳愣住,紧张得一动不动。
「你吐了一身,又淋了露水,该吃些热的暖胃。还受惊吗?」婉婉递过汤碗,语气温淡。
裴琳接过,低头呷了一口,汤暖,却烫得她眼眶微热。
「我……还是觉得很愧对妳......。」
裴琳眼泪夺眶而出,颤着声道:「我不是有心的……我只是……我怕,我真的很怕,他从来没那样看过谁……」
婉婉轻叹一口气,将汤碗接回,替她擦去眼角的泪,道:「裴玄是个好人,他知道你重要,也会一直护着你。我亦也是,因为这军中的每个人,都想活下来,我们要珍惜彼此。」
裴琳抽泣着,像个迷路的孩子:「我可以把妳当姊姊吗?」
婉婉闻言,终于轻轻一笑,温声说:「当然。」
裴琳终于缓下泣声,耸拉着头又问:「婉婉姐姐......那妳......对玄哥哥......是什么想法呢?玄哥哥对妳,我是知情的......因为我一直看着他,所以......我清楚,妳对他来说一定很特别,其实你们真的很般配,只是我在心底不愿承认,但现在......我很希望妳能接受他的心意。」
婉婉低头沉思着,是啊,他到底对裴玄是什么感觉呢?
「我……其实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喜欢。但我每次见到他,心里就觉得很稳当。像风再怎么乱,他站在那里,我就觉得不会倒下。他说的话、做的事,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。一旦他站在我身边,我就开始想,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,那该有多好。」
随着语毕,婉婉才恍然发现,是呀,这不就是喜欢吗?谁说喜欢一定要如同她和赤狄王般轰烈,喜欢也可以细水长流,不是日日思念得辗转难眠,也不是见面便心跳如鼓。而是当她疲惫时,只要想到他在,就觉得撑得下去;是他一句话、一个眼神,能让她安定下来,哪怕外头风雨如晦。
那种踏实,不张扬、不炙热,却如春日暖阳,润物无声。
婉婉垂下眼眸,轻声说:「不……我已经,不再只是依赖他了。」
她笑了笑,眼底浮着一抹温柔:「我想……我也在等他走近我,只是自己没察觉而已。」
火光映照下的裴琳没有出声,只是看着她,忽然弯起眼角笑了。
「那我可要快点放下他了,不然万一就此错过好郎君,我可后悔都来不及了。」
婉婉闻言也笑了,笑意却带着一点微酸——原来她早已心动,只是直到此刻,才真的懂了那份悄然滋长的情意。
「我去看他的伤势如何了。」方才,裴玄舍身挡箭之时,婉婉感到心脏狠狠被什么刺了一下,一种陌生而汹涌的情绪从胸口翻涌而出。她从未这样慌张过,也从未如此害怕失去一个人。
那不是恐惧,那是心疼,不是为他受伤的血肉之苦,而是心疼他的决绝与毫不犹豫。
只是因裴琳惊魂未定的模样实在太过怜人,整个人发抖不已,裴玄也是交代她先安抚好表妹,他会即刻请军医来治疗箭伤,让她不必担忧。
如今这边心结已开,她是真的迫不及待想去他身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