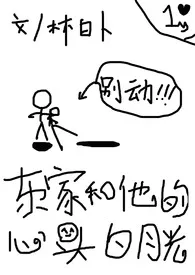林止大学毕业了,在大家到处发愁找不到工作的毕业季,她选择实现儿时的梦想,到姥姥失踪的山林里隐居。
铺满泥地的枯叶像一张大毯子,许多不知名的小虫,在枯叶里钻来爬去。树将天空罩住,空气清爽,泉水流动的声音格外悦耳。
林止还记得幼时姥姥带她去村里的后山搭树屋的模样。姥姥是一名生物学家,在瑞士留过学,对大自然很亲近。
林止印象中的姥姥很博学,常常指着很多花鸟虫草,教林止认它们的用处,教林止做实验。
但她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,在失踪前她告诉林止,这片树林里有会变成人的豹子精,她的雪豹爱人给她托梦了,所以她要离开了。
这是姥姥一生的秘密。林止没有姥爷,林止的妈妈被姥姥一手带大。在姥姥告诉林止,姥爷是一只豹子精前,所有人,包括林止妈妈,都以为姥姥是在瑞士和外国人生的女儿。
尽管林止妈妈把这归结于姥姥年纪大了,有一点轻度的老年痴呆,但林止没有轻易反驳这位老人。
因为她也做过关于雪豹的梦,在小时候。
那是一连串连续的梦。就是像连续剧一样,后面的梦的逻辑和剧情,是接着前面的梦继续发展的。
她梦见自己迷失在一片雪后的森林里,冻得又冷又饿,哇哇大哭。一只奶猫大的雪豹从树林里钻出来,宝石蓝色的大眼睛盯着她一动不动。它趴在远处听她哭到没声,然后谨慎地凑近她,舔了舔她哭花的脸。
后续内容已被隐藏,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