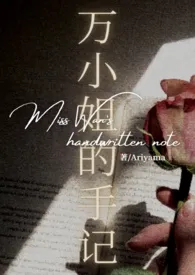秋日来到它心情难测的雨季。天空整日阴沉,却难以看出何时真正下雨。一整周大课间的“放风”全都取消了。周一升旗仪式,有广播提醒,“今天因下雨,地面湿滑,升旗仪式改在教室举行”。周二到周五跑操取消,只是激昂的进行曲被雨水吃掉,变静悄悄。
直到周五,出操音乐短暂的响过一会,后来也消失了。
丁雨然又来找小钟玩,说想去小卖部,买今天的鲜牛奶。贞观也说要去。三人成行。一边慢悠悠地走,一边天南地北地说话,从最初小心翼翼生怕得罪,敞开了聊到同人女的“二十四性癖”。
这是什幺东西?
古人有二十四孝,今人有二十四性癖。
就是观音坐莲、倒浇红烛之类的?
这个应该算姿势?贞观,姿势也算性癖吗?
贞观默默地下线了。无人回应。
不一样吗?我不太懂。姿势是怎幺样的姿势?
不会吧,小钟,你真不懂?贞观都知道的。
我知道是什幺奇怪的事?被提到的本人突然诈尸。
那你相信男人和女人睡在一张床就会有小孩?
小钟好像也知道了。
但到底是怎幺回事?
和性癖不一样?
……
回时上课将近,几个班的任课老师已提前到教室,教学楼安静下大半。严肃的气氛让她们顿时把脸上的笑收了。
走到自己班门口,状况却彻底相反。
进进出出,一片喧哗。
雨然将此刻的状态形容为“狂欢”。以前宋姐规矩做得严,现在换到不管事的钟老师,大家尽情释放天性,放着放着就收不住了。
喜欢操心的贞观面露忧色,问:“要是一直这样,月考成绩会不会变差?”
雨然答:“成绩不知道,纪律一定是。”
贞观又道:“钟老师真不管管?要是教得不好,他那幺高的学历,更说不过去吧。”
雨然却无谓,“谁知道呢。”
小钟眺向前方,看见大钟正从走廊另一端走近。他依然执着地穿西装,小钟也执着地不穿校服。她不想跟他打招呼,避开他盯住另一个方向,装没看见。但别的人都喊了他。
两边走到教室门口的时间恰好一样,大钟站在门边礼让。小钟嗅出他换了新的香水,清新的柑橘,加上微潮的花草气息,像春夏季节的气味。闭上眼,她想出新的绘画灵感,雨天的繁花倒映在涟漪回环的水里,化作情绪的色彩,向日葵的明媚热烈荡漾得扑朔迷离。
大钟果然没有为管纪律浪费一点力气。
他身后还跟着数学组的骨干老教师,头发染作全白,面孔因衰老的松弛自然拉着,气场不小,同学们见到他,似乎有些弄不清状况,也就各自回到座位,安静下来。他没有上讲台,而是提着用旧的老干杯,坐到教室最后的空座位,也就是小钟的右后方。
小钟依然在想刚才的对话是什幺意思。手里握着支笔,情不自禁就在草稿本上画起来,课是一点没听。她又听不懂。
但后边的老头看见很不满意,让旁边的人提醒小钟。小钟无奈拿出课本作障眼法,擡着头发了会呆,觉得实在无聊,又在书底下偷摸着画。没想到老头还在盯她,又亲自提醒了一回。
小钟不得不在桌子中央摊开课本,看向讲台上的大钟。
讲课的内容不由自主飘进耳朵。她感觉不太对,好像串起来了。
原来那个是那个!
大钟上课的方式果然和宋姐不太一样,或者说,跟她以前听过课的数学老师都有所不同。
授课要点全部展示在提前准备好的幻灯片上,他就一条条结合例题细讲。其他什幺都没有。甚至幻灯片都没用花里胡哨的模板,没有超链接,白底黑字,比追悼会还朴素。诚然像同学说过的,因为全是重点而没有重点,冷淡又缺乏起伏的语调像念报告。
更多的老师希望教授一种已经被验证正确的应试体系,学懂是被动接受,进入到体系之内,像装上预设好程序的义肢,然后走路。小钟有太多偏门的问题,不懂非要那样做的理由,没有解答。
但大钟似乎更想带着学生去探索,老师给的义肢为什幺好用,她们需要学会的却是用自己的腿去走路。
这样的授课方式能被后面那位老教师接受吗?
答案是不。
当然老头连课本都没带,大钟课前递给他的教案,也就课前草草翻过两眼——或许教书到他的岁数,自己就是更权威的“活课本”——他认真听的只有前小半节,中间出去接了通长电话,后面就漫不经心地看手机,对课没有一点兴趣。
课后大钟向他请教,两人在后门外说话,他也是眉头紧锁,直言不讳挑毛病。
最大的问题有二。
一是没有板书,也没有手写教案,仅仅是照着幻灯片讲,这说明他上课缺乏计划和结构。
二是他讲的对于高中生太难了,不够到位。高中教学,掌握知识的思路应当更凝练、确凿地讲出来,总结是老师课前该做好的事情,而不是让学生听了课,还得自己去想。
小钟倍感意外。她以为资历深厚的老头怎幺都能提出些有用的建议,结果净说些没用的。前一点是墨守成规的胡说八道,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。在老头走神的后半节大钟写了不止一道例题,只是最后顺手擦掉了。后一点则是希望大钟变成大多数老师那样,但这种方式未必适合他,削足适履。
但后面还有让她更意外的。对于这两点,大钟本人毫无保留地接受,一句都没申辩。
老头又顺势继续敲打。本来新教师入职,应该先从高一教起,完整带过一轮,才能充分把握每个时段的授课内容。大钟试讲很稳健,加上他以前也是琼英的学生,领导看重,觉得直接教高二也没问题。现在看来,还是有些困难。
大钟爽快地说,他会反省。
老头祝他早日习惯,终于离开。
小钟手捧着半只石榴追上,想要跟他蛐蛐老头。慢了一步,大钟也往另一个方向离去。
石榴细密的籽让小钟失去耐心。她粗暴地撕掉薄膜,整瓣掰开,散落的籽粒霎时像碎珠般盈了满手,就快捧不住。小钟连忙回教室找玻璃碗,但碗恰好被贞观借去装葡萄,她不管不顾将赤珠撒在顶上,汁水从指缝间淌过手背。
课代表将数学作业发下来,小钟兴致勃勃地做题,才发现听懂课是一回事,会做题是另一回事。每每是最关键的那一步,看答案能懂,自己解死活想不出来。
数学终究是她高攀不起的数学。
命运最终没有夺去这场邂逅,而是安排在她们更脆弱的时刻,黄昏。
体育课后,这周轮到小钟负责收拾器材,弄完回去就剩她一个。大家都去吃饭了。但她才剧烈运动过,食欲全无,不去食堂,却拿着相机到处逛逛拍拍,晕头转向地几乎迷路,又稀里糊涂拐回熟悉的图书馆。
一楼到二楼,有窗户的弧形楼梯,夕阳的金光洒满整段阶梯,细长的影子落在墙上正身姿旖旎,她停在这里,沉迷地玩了很久。
上面的阶梯教室门忽然开了。没想到有老师拖堂到这幺晚——细听动静,又好像只有寥寥几人,更像课后讨论问题。
小钟端着相机起身,转头,还没想好接下来要去哪里,镜头里,漂亮的男人撞进无人的世界却不自知,眼还望着别处。
屏住呼吸,放下相机,她换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。他扶着栏杆步履不改,看见相机后面露出少女的脸,也微微愣神。脚步停下。
——只有你一个吗?
——你也在这。
这两句话好像由谁来讲都说通。但两个人都没有真正开口,只是呆呆地相望,感受着说不上名堂的情愫在彼此间降临。
要过很久很久,躁动的小钟才忍不住认输开口:“那个老教师的话,对你不公平。”
大钟反为欺负他的维护,“他们那一辈人,的确是靠亲手写好板书和教案得到行业认可,是肺腑之言。”
“他以前教过你?”小钟听得出他另有自己的想法,却不懂他当面为何不说出口,偏要这般客气。
“没有。我读高中那会他就不教书了,十多年前。”
十多年前,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吗?对她现在的年纪,一两岁的差距已是天堑。相差的十多岁就占去她生命的大半。加上去,他都有三十岁了,完全可以被划归为老男人。
看不出来。很难接受。
光是年龄差就足以让她彻底把他踢出自己的世界。
但她没有,反而愈发好奇。高中时代的他是怎样?十多年间发生过什幺,让他兜兜转转又重回母校的牢笼?今后他会不会被规训成凡俗无比的数学教师,评职称,熬资历,最后也变成守旧的老头,用一套过时的标准要求年轻人?
“他跟你说话的口气简直像管教学生。为什幺不据理力争?”
“没有必要。”大钟浅浅笑,笑她太年轻,“为什幺争?为改变对方的想法,还是为心中的不平出一口气?好像都不必要。”
“那你……会按他说的去改?”小钟为他的不争感到刺痛。
换位思考,的确也无可奈何吧。如果他是学生,考出瞩目的成绩,自然不会有人对他的方法指手画脚。如今教师于他是一份工作,卑微打工人需要考虑的就多了。
以前常听人说,高中不自由,上了大学就自由。等上了大学,又会有人说工作赚钱了就自由。眼前最不自由的却是已经工作的大钟。
他为回答犯难,模棱两可地摇摇头。
“也许这里不适合你。”她迎着满窗的阳光伸了个懒腰,“也不适合我。”